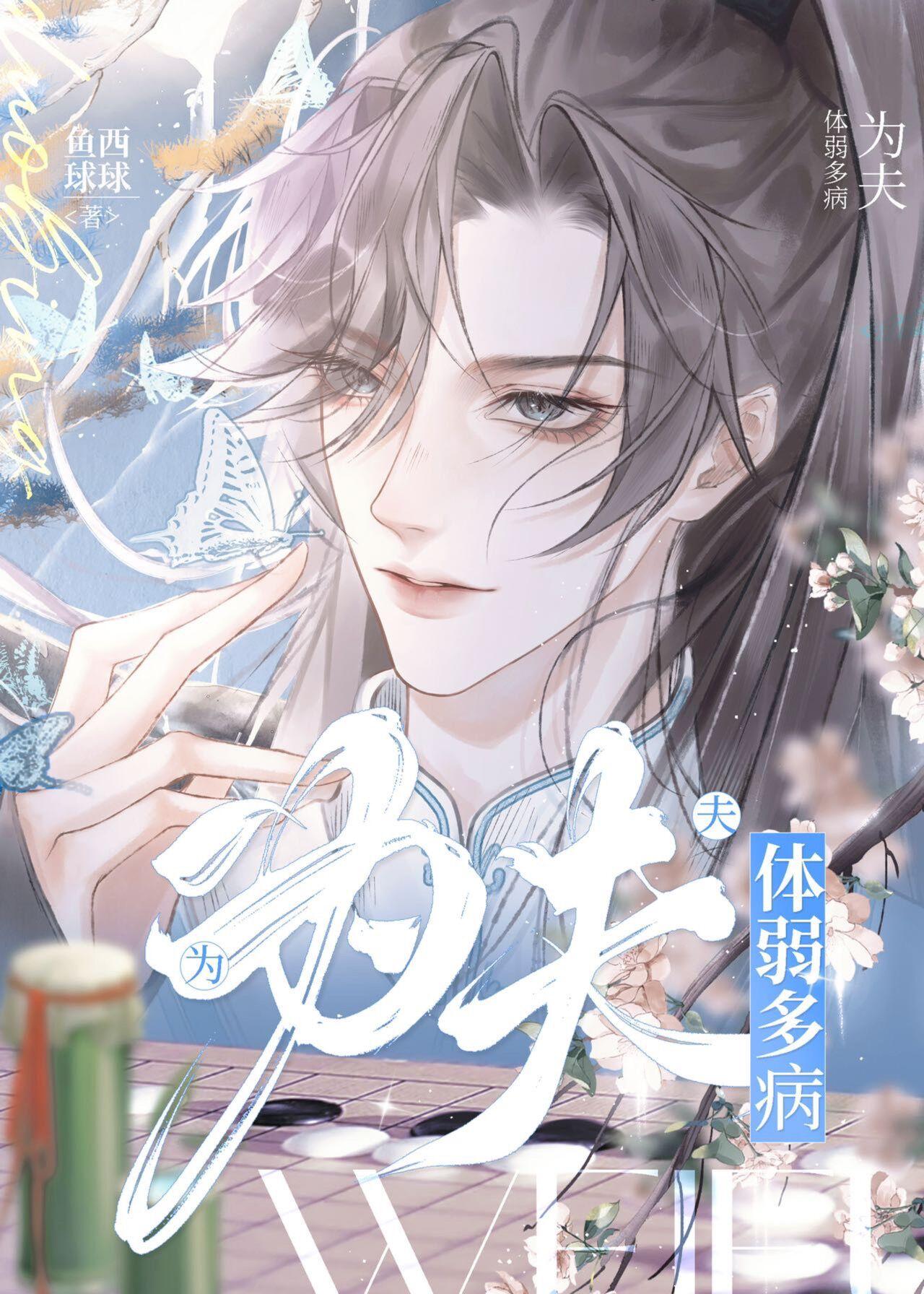EXO小说网>征途实录启航1926蓝烬 > 第20章(第1页)
第20章(第1页)
但这种选择,对于军事上的好处就很大了。攻击一个相比以前,面积扩大了五倍、而且受到相当的绿植掩护的城市,需要的战力可不仅仅是翻五倍的问题,也许要增加到十倍甚至二十倍。
所以这种策略,在有限战争的情况下会很有用。当然如果是美苏全盛时代,有能力发动那种几乎是无限制的饱和原子弹的战争,那么整个地球都可能重启,自然一切都不用去考虑了。
综合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卫这两大参照系,本来就不存在最优解,但也许李思华的这个想法,可以是次优解。牺牲了少量经济上的效率,比如说降低了10%的效率,但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上的安全性,例如是15倍。这种交换比,李思华认为是值得的。
当然,城市增加的工程建设,肯定巨大,不过前世那种“基建狂魔”的产能过剩印象,让她觉得到一定时候,这种建设并不一定是个大的问题。而且,基建技术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之前,各种土办法也不是没有效果。
单个城区在地理上,也应该在不太影响内部交通距离和便利性的前提下,尽可能地复杂化。棋盘式的方格街区布置最简单,也最有利于管理。可是这样的格局,在军事上,简直就是为敌军的攻击,自己画好了被炮击的目标网格。
如果按照这种地理布局,那么城市应该如何进行功能分区呢?是让每个城区自由发展吗?还是坚持规划优先,将同一功能的尽可能划分到一个城区?
李思华认为,规划优先是必然的。但是否将同一功能集中化,则要根据不同的产业情况。例如教育,不如集中在一个教育城的片区里;例如日用品,可以自由选择;例如军工,为了生产效率,应该集中到一个地理上最复杂的城区,比如靠山入地;例如造船,如果不集中到某个靠海的城区,根本无法组织起来。至于服务业,是由每个城区的人口规模所产生的需求所决定的。
大工业天然有集中性的需求,扭曲了自然规律也解决不了。前世的方法是,对于大工业,通过三线建设,在内地山区备份了一套较小的体系。而让此前依托大城市而形成的大工业体系,自由生长。以这种“1+1”的格局,来形成战争时期对大工业体系的保护。
李思华知道,在城市这一部分,她讲了太多的远景,在目前的海南根本实施不了。但她希望的是,通过这种对于城市的战略规划的讲解,让同志们理解我们的城市,应该如何管理、发展和建设。
现实是很残酷的,目前海南的城市,海口或者文昌这样的,基本上都是“商贸型”而非“产业型”的,说白了就是由于基本没有工业,这些城市都是贸易集市而形成的,所以商人及其贸易就构成了城市的命脉,而不是很多西方城市中,由已经形成的工业及其它产业支撑的城市经济。
这就涉及了另外一个大问题,对商业和商人的管理。
李思华是有心理准备,在这个部分她是需要暂时妥协的,因为海南还缺不了与外界的贸易。
按照西方的理论,贸易的逻辑是“比较优势”,意思是你生产的某种产品,成本比别人高,你就应该进口,这样会节省你的成本;如果你生产的另一种产品,成本最低,你就具备比较优势,应该出口,可以打败别人,赚取利润。
大家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贸易,就可以获得多赢。进口的都是自己高成本的东西,而出口的都是自己低成本的东西,大家都得到了好处。当然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,你又需要,那自然应该贸易进口。整个理论看上去很美。
然而这只是书本上的逻辑,也掩盖了通过贸易来剥削的本质。现实中的商业,要比这残酷得多。就中国目前的商业而言,看得到的最清楚的现实,就是“低买高卖”,商人的主动权和定价权,远远超过了提供商品的工坊和农民,这是不对等不公平的贸易关系。
例如对于农民生产的稻谷,在收获的时候,商人会拼命压低价格,甚至联合起来,用超低的价格收购;而他们运到销售目的地的时候,却会拼命抬高价格,囤积居奇,炒作宣传。以此来实现他们居间,获得高额的差价利润。所以有人认为商业其实就是战争,是商人对生产者的战争,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。
我们的对策是怎样的呢?对于我们能提供的商品,是比较有主动权的。我们设立物价部门,就是为了形成根据地统一的物价管制。管制物价如何形成呢?物价局应该调研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劳力成本等整体成本,加上合理的利润后形成。这就是定价权。
商人要从我们这购买,就必须尊从管制物价,要不我们就不卖。而商业部门除了管理商人和商业外,一个重要职责,就是对我们自己内部消化后,有剩余的产品,在如果商人不买的情况下,自己寻找销路,不低于管制物价而卖掉。
对于我们需要买入的商品,主动权就没有那么大。商人可能出高价,在没有办法的时候,我们也只能接受。但我们应该尽量地开辟多元化的采购渠道,例如采取招标方式,让商人比价,或者寻找其它的采购途径等,发挥自己的主动性,取得采购商品的合理价格。
最复杂的是,需要根据对需求的把握,来控制商品的生产,每种产品的需求不是无限量的,例如我们拼命发展大量的茶园,就可能导致有过多的茶叶,卖不掉。好在现在还处于早期,现在的问题不是产品太多,而是生产都还没组织起来。商业上的同志们,要在实践中摸索经验,与商人们斗智斗勇,保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。
同志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是,无限制的商业,对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性。中国历代王朝,没有不对商业或者商人去做一些限制的。有句话说:“无农不稳、无工不富、无商不活、无兵不强。”历代统治阶层难道不知道这个“无商不活”的道理吗?
他们当然知道,但他们更知道商人和商业的破坏性,因为财力上的巨大差距,如果不加限制,就会被商人掌握产品的定价权和话语权,于是提供产品的农民或者工坊,就会被破产、逼死,至少是穷困不堪,造成社会不稳定。
完全竞争的只有贸易,那是只存在于西方的书本上的,事实上,占据了定价权地位的一方,必然侵害贸易对手的利益,所以大多数的贸易情况下,本质是不公平的。
所以我们需要物价管制,以集体和组织的力量来平衡商人。而且我们之间的合作,是因为革命的当前需要而暂时的,长期而言,我们需要另外一套规则。
在这里李思华没有深入下去,因为彻底的变革需要等待建国,以国家的力量来实施了。
第34章大工业、教育和民族
农业是基础,对农林渔牧的综合发展,以及配套的加工业、小型工业的发展,也许能让我们实现第一步的,由无产阶级向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的跃升。然而,大农业只能让我们初步的“富”,不能让我们“强”,而且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,“富”也会受到资源总量的自然限制。
所以大工业体系,将是在大农业体系基础上的,让我们实现“强”和“更富”的关键。我们知道,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热武器,都是高价向外国购买的,这能够做到强吗?没有自己的军工基础,靠购买,我们有多少钱能够一直购买下去呢?如果人家不卖给我们,整个军事体系都可能崩塌。发展工业,是不容选择的核心革命任务。
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极端孱弱,就海南来讲,几乎还不存在。然而工业基础匮乏,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,更严重的,是完全缺乏发展工业的人力资源。我们必须是几乎在一张白纸上,开始画图。
但是一张白纸,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,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嘛。一张已经有图的纸,也许修改起来反而很麻烦。
工业的发展,在海南将分成两个部分。
第一个部分,就是前述的对于大农业的配套工业,这基本上是一个“小工业体系”或者说是“民生工业体系”。其特点,是以农林渔牧的出产作为原料,以满足和提升人民的生活需求而建设的初级工业。例如皮革厂、罐头厂、饮料厂、家具厂、砖厂、食品厂、服装厂、渔船厂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