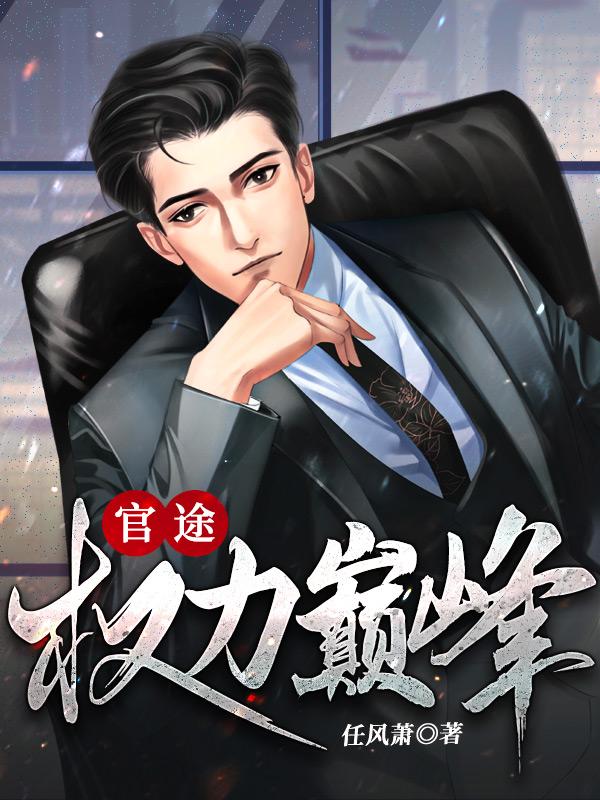EXO小说网>征途实录启航1926作者蓝烬 > 第43章(第3页)
第43章(第3页)
在他们出发前,已经预计到最危险的,就是要对抗敌军重炮对己方阵地的轰击。所以在卡车上携带了一些钢铁支架,尽量让修筑的工事能牢固一些。就算是这样,丁韶也心疼地看着一些局部的战壕,在重炮的轰击下崩塌。
超过3分钟的炮击结束,丁韶立即命令前线部队进入战壕,同样是一批人负责对抗,另一批人立即挖通被掩埋的战壕。
敌军的步兵,分开呈散兵线,开始进攻。越来越近,第一次他们还不了解我军,就让他们先吃一个亏。丁韶沉住气,100米、50米、30米,“开火!”军号声响起,重机枪、轻机枪、步枪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,二十门轻型山炮和迫击炮的呼啸声响起,而最前线战壕里的士兵们,几乎同时扔出手雷,发射掷弹筒,敌军的进攻一线部队中,到处是爆炸和血迹,整个队伍立即就矮了下去,在100米之内的几乎没有再站起来的,他们开始撤退了。
在敌军撤退后不到5分钟,敌军重炮的轰鸣声又响起来,丁韶已经尽量让前线壕沟中的同志们撤退到相对安全的地方,等待炮声结束再进入战壕对抗。
时间流逝,英军的攻势越来越猛,对于步兵的使用也不再吝惜,到了后面,甚至是接近于日本式的“密集猪突”,显然,敌军将领非常着急,而且他也不把自己手下这些印度军人当成人,如果是英国的本土士兵,想必他不敢这样做。
这就让丁韶压力如山,预备队一个接一个地补上去,前方伤亡很大。而战壕阵地越来越破碎,丁韶早已放弃了继续挖掘,而是每一次都临时让战士们挖自己的掩体,能保护自己就行。
他一直在接近一线的位置指挥,所以自己也很危险,上一次炮群攻击中,他的大腿被一块弹片割伤。在战斗的间隙中,他还自嘲地想着,差一点,我就成为我军高级军官中,第一位殉职的了,这大概不算是什么好名声。
又对抗了一次进攻,丁韶所部的伤亡已经很大了,他强迫自己不去想,慈不掌兵,必须完成任务。不过这个时候,传来了好消息,让15师全体士气大振。
丁韶事先的一记暗手,发挥了作用。
他事先组织了最精锐的一个小队,每个人装备卡宾枪和手枪,然后配置了若干掷弹筒和炸药包,让他们潜伏在比较远的地方,等待战斗打响过后,寻找机会,看能否突袭敌军炮兵阵地,或者是“斩首”英军的指挥部。这当然是一个近乎自杀的行为,可是同志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。
小队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,他们没有能发现英军的指挥部。可是英军炮兵群的位置太明显了,他们尽量潜伏到了接近的位置,然后忍耐下来,等到黄昏天色稍暗,而敌军步兵由于不停调动上前攻击,对于炮群的保护比较懈怠的时候,突然发动了袭击。
小队尽量地杀伤了炮兵,引爆了不少炮弹,炸毁了很多门大炮,等到英军反应过来围攻他们的时候,小队边打边撤,最后牺牲了一多半的同志。代价也是惨重的。
不过成果也是丰硕的,按照小队的汇报,他们至少摧毁了13以上的重炮,最关键的,是摧毁了敌军炮群的一个临时军火库。估计这样储备炮弹的军火库,英军能有2~3个就不错了。这将使得接下来英军的炮群打击,威力大减。
消息传出,丁韶15师的同志们一片欢呼,他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
对面英印军的番号也是15师,还有16师。两个师的师长菲尔德和斯托克,这个时候正在焦虑中,已经是晚上,很难掌握进攻,而且对方虽然没有重武器,但是非常顽强,士兵训练有素,士气明显很高,不是能够马上压倒的敌人。
所有两人商量之下,决定要绕开前头的敌人,向东攻击前进,绕行回到仁安羌。这个新方向缺乏公路,一些重炮就只好丢弃,但也没有办法,他们也知道,敌军在此拼命阻击,肯定是援军已经不远,他们如果不赶紧跑,就有可能陷入重围,导致全军覆没。
英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格外凶猛,重炮的数量虽然少了,可是这一次,他们完全不吝惜炮弹,足足打了10分钟,此前的进攻一般都是3分钟左右。在炮群攻击后,大队的步兵也变得格外凶狠,丁韶的15师,几乎将预备队全部投入,最终才把这一波敌人的攻势压了下去。
丁韶心中有点猜测,但不敢确定。
这一次的敌人攻势后,战场显得格外宁静,连冷枪都很少。敌军的阵地很快开始喧嚣起来,有侦察战士来汇报,英军撤退了,方向向东!
丁韶立即明白了敌军的意图。但是他现在陷入了两难,由于敌军重炮的攻击,他的伤亡,并不下于英军,离开工事防御体系,去追击敌军的话,可能会被敌军反扑。但是如果不追击,我军的援兵,什么时候能赶到呢?
仿佛是心有灵犀,徐向前的最新电报终于到了,他们已经赶到了附近,离开战场只有几公里了,丁韶立即汇报了最新的情况。
徐向前让丁韶继续坚守阵地,封闭这条出路,而他的五个师大军,则像一把扇子,向着英军2个师逃跑的方向扇了过去。
大约不到半个小时,丁韶就听到了东面枪声开始响起,然后越来越密,打成一片,而接下来,更是有大炮的声音轰鸣,火光冲天,让半个天空都变红了。他叹了一口气,可惜不能参加这最后的决战。
这场围歼战持续了几乎整个夜晚,一直到凌晨,还有局部在激烈战斗,但等到上午九点后,战场终于沉寂了下来,英印军第15师、16师,几乎全军覆灭,能逃出去的败兵溃勇,不到一千人。而两个师的师长菲尔德和斯托克,最后带着指挥部的军官们投降了。这也是我军第一次俘获如此高级别的英军将领。
在投降之前,菲尔德和斯托克向戴尔少将,以及缅甸总督英尼斯,都拍发了电报。
戴尔少将痛苦地低下了头,他知道,同样的噩运,很快会降临到他自己的身上,要投降吗?他想了想,又摇摇头,在他这里,还没有经受战壕战的考验,如果不战而降,最后即使他能回到英国,那也会是无尽的羞辱甚至是牢狱之灾。现在,还是尽力一战吧。他隐瞒了消息,让军官们去激励士兵,我们的援军已经不远了,大家努力奋战吧。
英尼斯则是面无表情,他其实早有猜测。
英尼斯并不知道后世有一个著名的“墨菲定理”,但他几十年的宦海经验,给了他同样的认知: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,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,它总会发生。现在的情况,就是这条规律的证明。
这个时候伦敦的陆军部,已经是人仰马翻,一片混乱。
布鲁克部长面沉如水,缅甸简直是一团糟。2个师已经被全歼,而其余4个师,大概率也会是全军覆灭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英军还没有损失过如此大。显然,英印军面对的不是什么土著的反抗起义军,而是一只还不为英国所知的,拥有强大武装、严格训练和相当规模的现代军队。
我们以为是去剿灭叛乱,结果却是碰上了一场“国战”,布鲁克的脸上露出了苦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