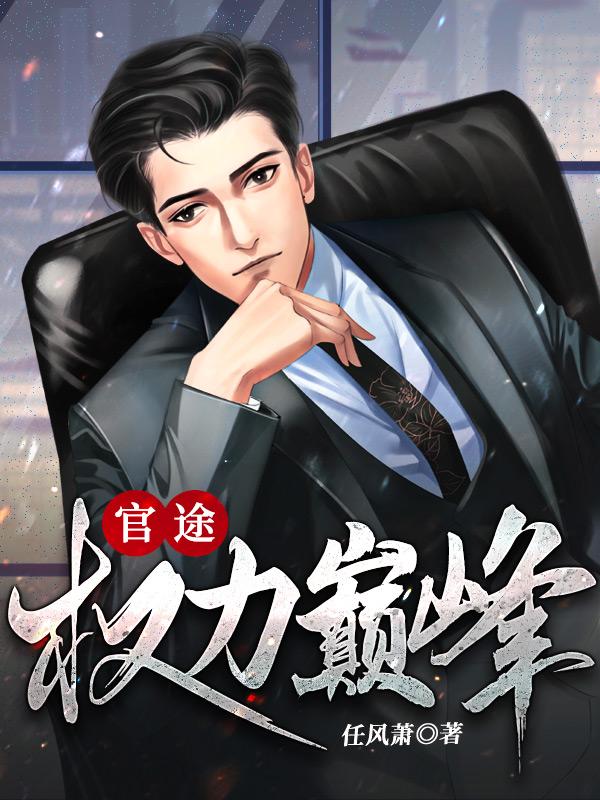EXO小说网>谁许长乐 > 外戚(第1页)
外戚(第1页)
张岁安回到张府时,夜幕已沉。
“公子,今日怎的回得这么晚?也不让轺车去接?”彭吉见他终于回来,连忙上前问道。
张岁安没有答话,他一路从宫门步行回府,走了整整一个时辰,却还是没能走清头脑,他心不静,思绪自然也如乱麻一般。
在他看来,自己不仅没能救得了小七,还顺道拉着父亲和好友一同入了局。
若一切到此为止,按照圣意编排,各自认命,可小七皇子便遁入了死局。
可若继续造势,一切都是未知数,若陛下当真雷霆之怒,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被卷进去。
彭吉的声音忽然挤入耳边:“对了,公子,你迟迟未归,客人还在后堂一直等你呢。”
“客人?”张岁安一愣。
“对,说是姓杜,酉时便来了,一直等到现在,想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吧?”
张岁安定了定神,便去了后堂见客。
杜何见张岁安终于归家,连忙将案上续了好几次的茶一饮而尽,起身道:“子康公子忙于修典大计,杜何今日不请自来,实在是叨扰了。”
张岁安见他神色急促,问道:“文德兄此来,可是有什么急事?”
杜何身后带了一个布裹,里头似乎扎扎实实地装了不少东西,他低了低头道:“公子,可否借一步详说?”
张岁安闻言,将杜何请去了自己的书房。
杜何将带来的那一袋东西放在地上,悉数铺开,竟是一大堆简牍账目。
说是账目,却更像是鬼画符,潦草程度堪比天书,像是自带了一层加密系统,除了写此天书的人,其他人未必能看得懂。
“幸而子康兄举荐,在下才得以入司农府,这是在下自入茶政司后,所经手过的账目副本,不是官本,是在下随手所录,故而有些潦草,若无在下讲解,谁也看不明白。”
这个杜何此前虽无仕途经验,但毕竟是个常年混迹市井的商贩,官场也是人场,只要是有人的地方,他都能油滑地找到空子趁虚而入。入职司农寺不到半年时间,不仅在茶政司上下混得通,还在粮、盐、铁署各自都认上了熟人。
“在下初入茶政司时,便发现入库的账册与实际库存有异,账册上写明的甲等首批春茶为三千斤,可库中至多只有不到两千斤,除了供给皇室的五百斤以外,其他全与陈茶混卖,可这名义上供给皇室的五百春茶,却没有少府的采买符节,只有司农寺丞的批复手令,司农寺丞批复后,再交由司农寺卿复核。”
杜何说至此处,忽而顿了顿,沉声道,“这司农寺卿的身份,想必子康兄也明白……”
大司农卿梁瑞,乃是太妃之弟,先帝皇后早年薨逝,那太妃便是当今景和帝的养母,说到底,这梁瑞还算是半个国舅爷。
官吏舞弊贪腐,皆由御史台监察,可如今的御史台由涂均掌管,这个涂均八面玲珑,对此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也难怪这些蛀虫嚣张至此。
张岁安眉头微蹙了蹙:“少府掌皇室私用,司农寺绕开少府,难不成这皇室用茶,根本没进内宫?”
“少府到底进了多少春茶,在下难以知晓,这朱楼背后是什么来头,能走皇亲国戚的门路,在下不过一小小官吏,就更不得而知了。”杜何顿了顿,继而又说道,“春茶到底非普通平民常得之物,他们才做得十分小心,除了这茶政之外,粮、盐、铁等更是变本加厉啊。”
杜何说着又展开一简“天书”——
“眼下正值蝗灾,赈灾粮管是当下司农寺的一大要事,上月太仓署缺人,在下捡了个空缺,便从茶署临时调任到太仓的粮署办事,除了南境两州以外,东面的宜州灾情也十分严重,尤其是会冶郡,五十万石灾粮,登记入册的损耗竟然过半,一来二去,轮到灾民手中的不到十万石,而那会冶郡郡守,又偏偏是那赵……”
杜何的话头戛然而止,唉声叹息,顿了良久——
会冶郡是赵氏的祖籍,陛下亲封赵贵嫔之弟赵显为会冶郡太守,或许也有让赵氏一族站稳地方势力的意思。
“说句犯上的话,这梁氏与赵氏同为外戚,行径又如此相同,难保以后不会是一丘之貉。”杜何语气小怒,接着又迅速平静了下来,埋头开始卷自己带来的那一方方简牍,“在下随手录的这些账目,也不是什么核心账册,都是些末微边角的碎料,作不得证据,今日专程来讲与子康公子听,是为报公子当日举荐之恩,为公子解惑,公子如今知道了,就当没听过,可万万不要将杜某供出去啊。”
“子康明白。”张岁安沉声道。
杜何叹了一声:“蝗灾已是天灾,可饥荒却是人祸,说到底受苦的还是百姓,我在会冶也有几门远亲,听闻今年粮荒,村子里已经开始易子而食了……在下官职微末,最多只能做到这份上了,子康公子身居要职,现任修典一事,又能上达天听,想必定是比在下说话要管用得多。”
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,文德兄此举已是大义。”张岁安的目光落在那一堆子的“天书”上,“只是御史台监察百官,奏本总要有个由头,不知文德兄可否提供一二线索。”
杜何闻言也是微微一怔,嘴唇抿得发白,似是在做着什么激烈的心理斗争。
半晌过后,他终于开口说:“之前与同僚们喝酒时,在下确实无意间听说了一件事,太仓署下曾有一官吏,对司农寺的风气甚为不满,于是偷偷向御史台写了检举的文书,不出月余,便因母丧而辞官回乡丁忧,路上不幸遭山匪劫杀,就此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