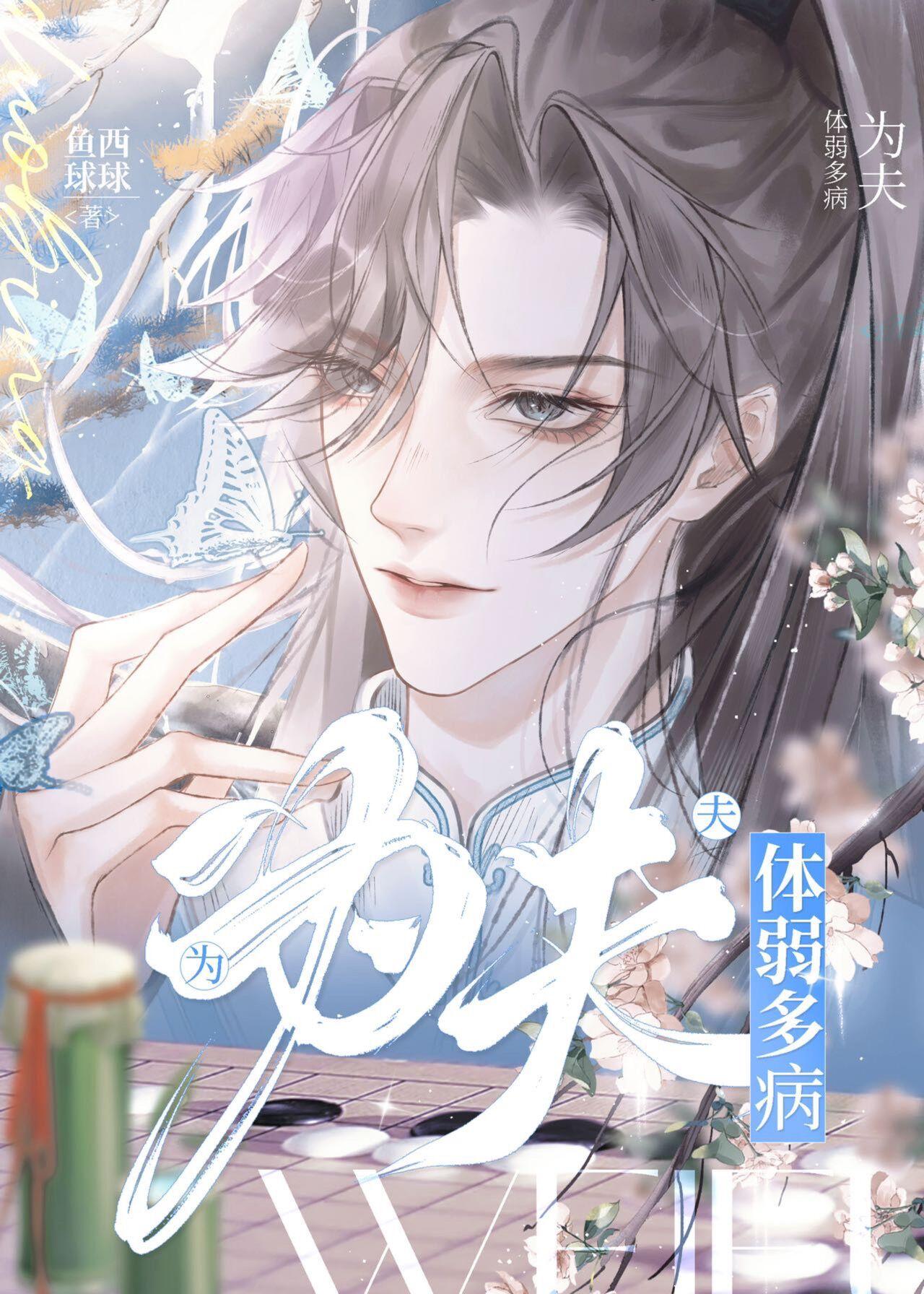EXO小说网>征途实录启航1926 > 第85章(第3页)
第85章(第3页)
当然,未来战争的进展,现在只能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计划,双方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变阵和调整。
但无论如何,河北既然是第一阶段最核心的目标,未雨绸缪就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正是余润群的重大使命。
余润群现在是在北平。
对他而言,这是一座颓唐衰老的都城。表面上北平的市容,在民国时代是极好的,尤其是从1933年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《塘沽协定》之后,民国用大片国土的丧失,换来了一段短暂的苟且偷生“美好”时光。
此时的北平市,大力发展面对西方旅客的旅游业,于是从1935年开始,对天坛、东南角楼、西直门箭楼、正阳门五牌楼、西安门、地安门、明长陵等一批“帝都门脸”,进行了修缮。曾有人描述这个计划让北平“焕然一新”:“在北平市中心登高一望,倒是金碧辉煌、衢道通直,一种新气象,反比帝制时代还要整齐些。”
这确实吸引了带着满满的优越感的西方猎奇游客,历史上,到1937年抗战前,北平的饭店和旅店床位居然都不够了,当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居然超过了100万美元。
除了西方游客,还有几千名居住在北平的西方人,他们当然对这个远东城市充满好感,因为他们的生活“像王侯一般滋润”。
例如《纽约时报》记者阿班后来曾经回忆,对他而言,北平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,简直就是“黄金世界”。每当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,回忆起这段甜蜜时光,他就有一种“怀旧的痛楚”:
“那时的北平社交生活,大约从未有复制,也是万难再复原的。除公使馆卫队外,偌大的北平,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。外币在这里值大钱,因此娱乐活动都是极尽奢华的。北平俱乐部、法国俱乐部、德国俱乐部以及八宝山的高尔夫俱乐部,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所在。京城城墙外数英里处,便是赛马会,更是个快乐无比的地方。西方人,几乎人人有能力,在西山租个废弃的小寺院,作为避暑的别墅。秋日来临时,打野鸭、野鹅也是件乐事。野鸡和鹌鹑都极尽肥美,往往损坏庄稼。冬天时,总有三个月可以滑冰。”
就在这些西方人,借助母国帝国主义的势力,在北平尽享优越生活的时候,北平底层人民的生活,却是极端困苦的。
失去了民国首都的地位,少了中央财政的资助,少了很多达官贵人,这座城市就显现出了它的明显弱点。北平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,工商业都无甚可观,三十年代整个北平的产业工人,居然只有7000多人,社会经济全部是商业和服务业。所以李思华前世,听说过广州、香港和上海的工人运动,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北平的工人运动,因为此时的北平,哪有什么工人阶级?所有的运动,都是学生和市民的运动。
在不同人的眼里,就有着不同印象的北平。有人认为这是民国的黄金时代,充满着“人间四月天”的浪漫气息,但在余润群这样的革命者眼里,就这是一座帝国余晖之下,已经散发着恶臭的衰败城市,无数的贫民,例如那些人力车夫,每天出尽全力,也挣不到能吃饱饭的钱。一旦生病,就可以宣告这个可怜的家庭完蛋了。160万人口的北平市,赤贫的人口至少超过了50万。
这样的北平有什么美丽可言?又有什么眷恋可言?余润群的内心发誓,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一切!
东北,哈尔滨。
一处典型的东北宅院内,大炕上盘坐这两个人。其中一个人的口音是满嘴的东北“大碴子味”,而另一人,则是山东口音。
那位满嘴东北大碴子味口音的男人,名叫李为民。他是哈尔滨的地下党员,最重要的职责,就是承担着为东北抗日联军购买炸药原料的任务。
他最出名的事迹是,由于无法在日伪军眼皮底下直接购买炸药,李为民找到不少西药店,说要买大量的硝酸钾。那些掌柜的当然很奇怪,但他的解释是:“我是从依兰来的,当地几个大药铺的老板,听说日本人马上要采取新的政策,以后这些货不能一次性买太多。所以他们托我,想一次从你这,多采购一点,以后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在非常充分的理由下,而且他在谈吐中,还能显示出对药品行业的熟识,这些药店的掌柜都相信了他。这样他就不断采购到不少制造炸药的原料,然后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联地区去。
所以李为民是一个冷静睿智的地下党员。
他已经确信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男人,确实是中央的特派员。因为此人正是以前一位他认识的同志,而且随身携带了精巧的电台,以及一些中央领导写给满洲省委一些同志的信件,尤其是刘少奇同志的字迹,他是认得的,因为刘少奇曾经是满洲省委书记,当时他直接受刘少奇同志领导,对他的字迹很熟悉。所以在阅读之后,他立即确信这位同志不可能是叛变后来找他钓鱼的。
中央特派员的到来,让李为民非常兴奋,因为在中央苏区红军长征以后,满洲省委和抗联的同志,就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。现在中央直接找过来了,以后东北的抗日活动,就又可以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了。
不过他当然也有疑惑,中央怎么知道他在哈尔滨呢?还知道他化名“王一民”?所以因为不知道其它同志的下落,先寻找的他。
中央特派员项明内心其实也有同一个疑惑,中央是怎么知道李为民的下落的呢?
这其实是李思华偶尔想起来的,前世她很喜欢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那部小说,其中的主人公“王一民”,她还去查过历史上有没有真人的原型,结果还真有,历史上我党三十年代在哈尔滨,确实有一位化名“王一民”的地下党员,真名叫李为民,承担着重要的地下工作,解放后还担任过鞍山市的市长。
所以她就将这个线索,提供给了负责联系东北抗联的刘少奇同志。他正苦思冥想,要用什么方法尽快与满洲省委联系上呢。
项明是刘少奇同志的秘书。他曾任中共地下党济南市委书记,在1932年在山东被敌人逮捕,可巧1933年的时候,在山东负责移民工作的洪国光,在工作中了解到有一些共产党员,被关押在济南和青岛的监狱里,于是组织了营救行动,项明就是其中被解救的一员。
这一次他受刘少奇同志的委托,来联系满洲省委,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,日本特务非常猖獗和狡猾,在哈尔滨的同志行踪都非常隐秘。能够找到李为民,简直是意外之喜。
至于他个人,虽然带着五六名伪装的特种战士,但是在这种敌占区,仍然是非常危险的。
他向李为民,介绍了中央与西华合并后,现在的大发展,李为民当然极为兴奋,他们在哈尔滨这里的敌占区,虽然从报纸上有个西华,但并不知道那就是新的中央。西华居然已经占据包括缅甸在内的九省之地,革命胜利的黎明,已经近在眼前!
李为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,举起茶杯一饮而尽,他要用这样的动作来平抑自己的激动。
在李为民的联系下,将电台送到了此时满洲省委负责人小骆(张文烈)的手上。因为1935年4月,杨光华与宣传部长谭国福、组织部长赵毅敏去了苏联,此时的满洲省委工作,由团省委书记小骆(张文烈)主持。